文/鄭紹彬 台中慈濟醫院外科部主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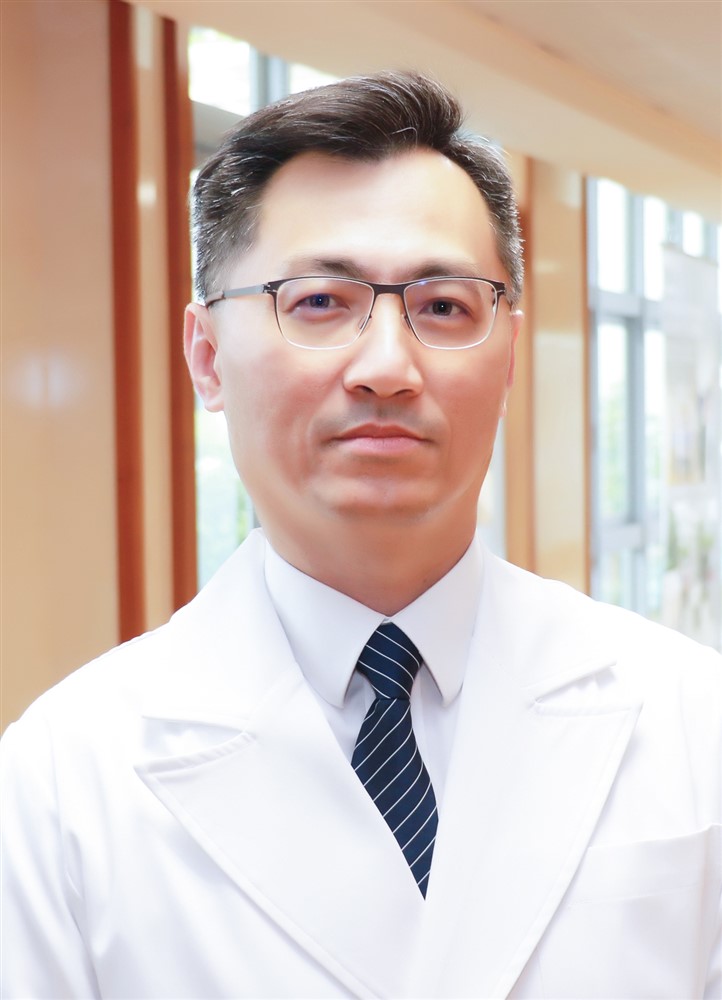
在醫療領域裡,倚賴多專業團隊的協力合作,拯救生命,診斷治療疾病,讓病人恢復健康,醫療團隊中,最至關重要的角色莫過於是護理人員;西班牙語中的護理師「Enfermera」,這個詞的來源為拉丁文中的「infirmarius」,意指為老病殘弱者(infirm) 的守護者(-arius),真實貼切地闡述了白衣大士的角色,不僅協助執行醫師所制定的醫療計畫,提供病人專業的護理照顧解除身體上的病痛,更時刻關注病人的需求,給予心理上的支持撫慰,陪伴他們走過生命的低谷。
從事肝臟移植二十餘載,醫治末期肝病的患者,術前的等待是與器官衰竭的拔河,拉緊繩索為患者爭取等待器官的時間與機會;移植手術是一場和時間賽跑的任務,從摘取器官到植入新肝,分秒必爭;術後的照顧則是另一場和感染與器官排斥對抗的硬仗,從術後初期的重症照護到恢復期的生理與心理的護理與衛教,讓每位移植病人能夠順利恢復健康,重啟第二人生。移植醫學的工作往往都是冗長且繁瑣,一路走來,每一個環節都仰賴許多護理人員不辭辛勞地無私奉獻,點滴在心頭。兩年多前到台中慈濟醫院草創肝臟移植業務,陸續完成屍肝移植及活體肝移植,過程中各個單位白衣大士的專業能力與發自內心的人文關懷,都讓人深深感動。

2022 年底開始草創業務之際,手術室、加護病房和一般病房的護理人員,就積極地邀請講授相關的課程,上課的時間都是清晨或是傍晚的非上班時段,有些人必須早起頂著清晨的寒意提早到醫院,有些人則是在辛苦上完八小時的白班後,自願留下來;即使過去從未接觸過這樣的醫療業務,她們仍然不畏困難地學習備戰,記下每個細節,與醫師討論如何執行各個場域的照護。隔年二月因緣俱足,台中慈院完成了首例的屍體肝臟移植。手術前一天,手術室護理師再三地與移植醫師確認盤點,將器械用物準備齊全,手術當天更是發揮了平日訓練有素的專業與團隊協作能力,無論手術室或是麻醉護理人員,都有條不紊地彼此合作,甚至在忙亂之餘,有許多護理師仍在下班後自願留下,堅守崗位,這樣並肩作戰的團隊精神,讓我深深地感動,心中更加篤定台中慈院這個大家庭有能力面對器官移植的挑戰。
術後,受贈患者轉入第二加護病房;同樣地加護病房的護理師在前一日也做足了環境準備,布置好正壓隔離病房的用物與事前的消毒。術後一週的重症照護極為繁瑣,護理人員每兩個小時要記錄回報輸出輸入量,還有各種藥物的輸注、抽痰、翻身擺位與清潔、管路及傷口護理等等,這些工作看似與外科重症護理類似,但其實更辛苦的是,護理人員必須全副武裝地穿戴著防護衣帽,一對一地與受贈患者待在正壓隔離室,執行所有的護理照護,只有吃飯與如廁時間由同事短暫替手,每個護理人員下班時,額頭和臉頰都留有帽子和口罩的壓痕,那是令人心疼且感動的印記。這樣一對一的高規格重症照護,加重了護理人力安排的困難,除了主護人員辛苦,一起當班的同事也必須承接比平日多的臨床業務,同時要支援正壓隔離室內的各項物資補給與藥物血品核對和傳遞,不分彼此的齊心協力與共同承擔,成為移植醫師在術後照護的堅實後盾。此外,護理人員更貼心地關注著患者的心理需求,隔離室封閉的空間、重大手術的生理壓力與家人分離的不安,受贈患者往往較為沮喪低落,甚至出現譫妄;護理人員儘管忙碌,都仍然會與受贈患者閒聊片刻,使用護理車的電腦播放患者喜愛的音樂和節目,緩和他們的情緒;不僅體現專業的護理素養,更充分發揮了深厚的人文關懷。

受贈者度過術後初期的重症照護,轉入外科專科10A 病房繼續恢復期的醫療。相同的,為了確實執行保護性隔離,病房護理人員在確認受贈者自加護病房轉出前一日,也費心地進行病室環境及用物的消毒。在恢復期的病房照護階段,雖然不似加護病房以一對一的照護規格,受贈者使用的藥物種類繁多,引流液的記錄及補充,生命徵象及血糖監測與處置等等,主責的護理人員同樣必須穿著防護衣在病室內執行,也同樣地需要同事承接其他的臨床業務,10A 病房護理團隊同樣合作無間,展現了團隊的默契和專業。這個時期的受贈者需要進行規則的復健活動,初期較虛弱,難免力有未逮;護理人員忙碌之際,時不時給予受贈者打氣鼓勵,教導看護記錄每次呼吸訓練和床旁活動的成果,幫助病人建立信心,成為病人恢復最後一哩路的守護者。
藉著兩例屍肝移植的經驗,我們在2024 年10 月也共同完成了台中慈院首例活體肝臟移植,護理團隊在照護經驗上已有所累積,卻仍舊保持著視病猶親的溫暖。由於受贈者的雙側髖關節都接受過人工關節置換,右側髖關節更因化膿性骨髓炎而移除人工關節,使用骨泥作暫時固定,加上移植手術耗時長,在病人移動及擺位都必須格外小心。手術室的護理人員,在預先了解受贈者情形後,充分準備臥位的保護用具,更親自躺上手術床用身體感受病人的臥位是否安全舒適;如此鉅細靡遺的用心關懷,遠比任何專業經驗更難能可貴,也是我心中台中慈院白衣大士最溫暖動人的時刻。

